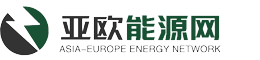记忆王为松:那张“多思和隐忍”的脸——追怀夏志厚老师

晚年夏志厚? ? ?
夏志厚是我们大学三四年级时的辅导员。记忆中他一直就是三四十岁、谦谦君子的样子,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七十多岁的老人。想想自己的年龄,老师怎么会不老呢。
夏志厚从安徽考到华师大,本来是要留校的,结果毕业时被错分配回了安徽,他也不抱怨,自己重新考回华师大,成为钱谷融先生的弟子,再次毕业,留校任教。他总是笔直地背着一只淡绿色的软布书包。他谨严,甚至是小心,经常跟我们讲的一句话是“凡事不要过杠杠”,读书和生活一样,都有底线。我去他河西的寝室大概也就一两次,可能因为夏天的缘故,他每回都是坐在寝室门口,因为人高,坐在小板凳上几乎就像坐在地上,在一张普通的四方凳上看书做笔记写文章。我们传阅过他发表的文章,可能就一次,《上海文学》上发表了一组“夏志厚评论小辑”。
青年夏志厚
三年级要写学年论文,我想写《再论“文学是人学”》。倪文尖说,你应该去跟夏老师聊聊,他既是我们辅导员,又是钱先生弟子,更主要在于他肯定会给出具体的意见建议,而不会推脱或者敷衍。于是,我倒是也满怀信心去了,刚报了题目,还不等我展开陈述,夏老师以毫无商量余地的口吻说:你不要写这个题目。我说,我想接着钱先生的题目往下写,加入新时期文学的内容,来补充完善这一论题。夏老师说,以你现在的学养写不了这题目。我说,那谁不是写了《“文学是人学”新论》吗。夏老师接下来的这句话,我确实是记了一辈子,也成为我日后经常告诫自己的一条“杠杠”:你没那才气。
左起:雷启立、倪文尖、王为松、夏志厚、李同兴? ?
我们毕业后没几年,他就去芝加哥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当编辑了。他写信问我,能否帮他找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翻译的厄普代克的《兔子三部曲》。我刚好买了内地新出的《兔子,跑吧》,于是提醒他国内已经有了译本。他说,正因为在他看来这个译本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,所以他才想到应该给国内的读者一个准确的厄普代克。
他来上海后,我带他见了一位资深外国文学编审,也是翻译家。我还记得当时老编辑婉拒的理由是,《兔子三部曲》中有不少露骨的描写,如果删去就很难体现作家的风格,但是保留不删,目前很难出版。从出版社出来,走在宽大的弄堂里,夏老师不说话,我也找不出话题,两个人颇有点尴尬地走到延安路的弄堂口。夏老师说,好吧,就这样,谢谢你陪我一下午。我说,我会再问问其他出版社。他说,不用麻烦了。
就此别过,再也没有见过夏志厚老师,也没再有联系。夏志厚去世后,学姐王晓丹在文章里说,当时她们女生圈子里觉得“夏志厚很有高仓健的气质,高冷沉默的硬汉气质”,并说他那“欲言又止的神态的确很迷人”。王晓丹说,“多年后,我在芝加哥遇到夏志厚,问他是否知道Y师姐早年对他的迷恋,他幽然一笑:知道,也只能不知道……问及他的个人生活,他说还是一个人。”
据说,他是芝加哥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唯一的中文编辑,十七年如一日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,从来没有走近咖啡机一步,也从来没有靠近临芝加哥河的大窗一步,新来的编辑跟他合作都会出一身汗,因为他会在下班前把你校样上的错字全部一一圈出,“夏老师的面孔阴沉下来,是不太讨人喜欢的”。即便是假日里带着同学去唐人街吃饭,他也是一个人大步流星走在前面,像是要甩开众人,等坐下吃饭时,他沉默着,偶尔浅浅一笑,看着大家欢声笑语。
典型的夏志厚说话行事的风格,话不多,直截了当,他只是说出自己的看法,并不打算与你讨论下去,但也绝不是逼迫你,他也不介意你听不听他的意见。当年他那句简单粗暴的“你没那才气”,让我一直觉得他对我的印象不好。但也正是因为这句断语,才使我后来说话做事常怀敬畏之心,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,因此勉力走到今天。一言一行,我总觉得背后有一双夏老师的眼睛,不动声色地看着我。
面对即将入学四十周年的我们,我希望那张“多思和隐忍”的脸上能有一丝哪怕一掠而过的微笑。
免责声明:该文章系本站转载,旨在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资讯。所涉内容不构成投资、消费建议,仅供读者参考。